放大资金,增加盈利可能
配资是一种为投资者提供杠杆资金的金融服务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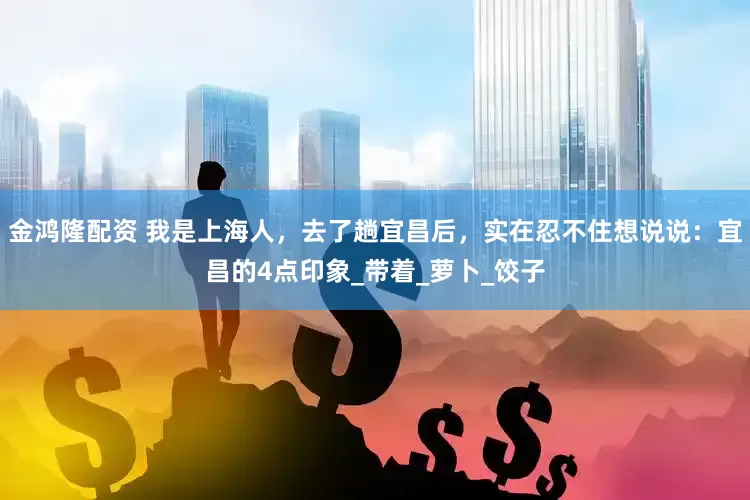
一、那水啊,绿得像块揉碎的翡翠
从虹桥机场起飞时,上海正下着蒙蒙细雨,高楼大厦在雨雾里像浸了水的宣纸,晕开一片灰蒙蒙的轮廓。我这上海人,看惯了黄浦江浑浊的浪,也受够了苏州河早年那股子腥气,原以为天下的水都带着城市的焦躁,直到在宜昌遇见清江。
头一日到宜昌,当地的朋友老陈开着辆半旧的比亚迪来接我,说先去清江画廊走走。车开出市区,越往山里钻,空气就越清爽,像刚拆封的薄荷糖。到了码头,坐上画舫,那水啊,第一眼看去竟让我愣了神——不是大海的蓝,也不是西湖的碧,是那种纯粹的、带着点奶白的绿,阳光一照,水面上浮着碎金子似的光,船划过去,浪纹像用毛笔蘸了青墨轻轻晕开,连船尾的白泡沫都透着绿。
老陈蹲在船头抽烟,看我扒着栏杆发呆,笑说:“没见过吧?这水从神农架流下来,干净得能直接喝。”我伸手去撩水,冰凉凉的,指尖沾了些,放在鼻尖闻,竟有股子山野草木的清甜味。想起在上海,周末去滨江步道散步,江风里总带着点柴油味,这会儿站在清江边上,看着两岸的山像水墨画一样铺展开,山上的树绿得浓,倒映在水里,连水都像活了似的,晃悠晃悠地把山影揉碎了。
船行到倒影峡,导游说这里的水最静,能把整座山都映上去。我凑过去看,可不嘛,水面平得像面镜子,上头是蓝天白云,下头也是蓝天白云,山尖顶着云,云脚浸在水里,分不出哪是天哪是水。同船有个带小孩的妈妈,孩子趴在栏杆上喊:“妈妈你看,水里有座山!”这话听着平常,可从那孩子嘴里说出来,倒像是说中了这江水的妙处——它不是简单的倒影,是把整个天地都揽进了怀里,柔得很,也深得多。
展开剩余80%二、城里的山,像块没劈开的豆腐
在上海,要看山得开车去佘山,那山矮矮的,爬上去半小时就能绕着顶走一圈,说是山,倒更像个大点的土坡。可宜昌的山,是直接长在城里的。
住在夷陵广场附近的酒店,推开窗就能看见对面的山,那山不高,却绿得密,半山腰还飘着几缕白花花的雾,像谁家蒸馒头的热气散错了地儿。第二天一早,我跟着老陈去爬磨基山,说是爬山,其实从市区走过去不过二十分钟。山脚下就是长江,江水在这里拐了个弯,浩浩荡荡地往东流,江面上有货船慢慢吞吞地过,鸣笛声拉得老长,在山谷里撞来撞去。
爬磨基山的路是石板铺的,有些地方长了青苔,滑溜溜的。路上遇见不少晨练的人,有牵着狗的大爷,有背着竹篓的大妈,竹篓里装着刚买的菜,还有几个中学生勾肩搭背地往上跑,嘴里喊着“快点快点,赶不上早读了”。老陈说,这山就是宜昌人的“后花园”,早上来遛弯,傍晚来散步,跟上海人去公园没啥区别,只是这“公园”里有树有鸟,还有长江的风。
爬到山顶,往下一看,我又愣住了。上海的高楼是挤在一起的,像堆起来的积木,而宜昌的城,是被山和水分开的。长江和清江把城市切成几块,高楼藏在山坳里,山呢,又探着头往城里看。你看那江边的楼房,最高的也就二十几层,不像上海动不动就摩天大楼,可偏偏这样,山和城才显得亲近。有座山的半山腰还修了步道,红色的栏杆顺着山脊走,远远看去,像给青山系了条红腰带。
老陈指着远处的西陵峡口说:“那边的山更高,三峡大坝就在那附近。”我眯着眼看,只见群山连绵,像水墨画里晕开的墨色,长江就从那山缝里穿过去。忽然想起秦岭,说山是“馒头”,宜昌的山没秦岭那么莽,但更像块没劈开的嫩豆腐,软软的,润润的,把城市轻轻托在手里,不挤也不压,让人心里头踏实。
三、萝卜饺子滚油香,凉虾甜得像春夜
在上海,早餐不是大饼油条就是小笼包,吃多了总觉得腻。可到了宜昌,头一顿早餐就把我吃服了——老陈带我去巷子里的一家小店,说要尝尝“萝卜饺子”。
我一听“萝卜饺子”,心里头犯嘀咕:萝卜做的饺子能好吃吗?上海也有萝卜丝饼,但那是酥皮的,里头包着点萝卜丝和肉糜。可宜昌的萝卜饺子不一样,是用一个铁勺舀了米浆,铺在勺底,放上切得细细的白萝卜丝,撒点辣椒面和葱花,再盖上一层米浆,然后放进油锅里炸。那油锅里的油是滚烫的,铁勺一放进去,“刺啦”一声,米浆瞬间就鼓起来,变成一个金黄的圆饼,边缘焦脆,中间软乎,萝卜丝在里头若隐若现。
我接过刚出锅的萝卜饺子,烫得直甩手,吹了半天才能咬一口。哟,那味道可真绝了!外皮炸得又香又脆,咬下去“咔嚓”一声,里头的米浆是软的,带着米香,萝卜丝吸饱了油香,又脆又甜,辣椒面的辣味恰到好处,不冲喉,反而把萝卜的清甜衬得更明显。我一口气吃了两个,连手指头都舔干净了。老陈在旁边笑:“咋样?比你们上海的萝卜丝饼带劲吧?”我连连点头,心里想,这哪是带劲,简直是把烟火气炸进了骨子里。
除了萝卜饺子,还得说说宜昌的“凉虾”。这可不是真的虾,是用糯米粉做的小吃,形状像小虾米,泡在红糖水里。我在滨江公园的夜市上买了一碗,红糖水是现熬的,带着甘蔗的甜香,凉虾白白胖胖的,嚼起来糯叽叽的,咽下去的时候,喉咙口都是甜丝丝的。那天晚上,我坐在江边的台阶上吃凉虾,江风吹过来,带着水汽,远处的三峡人家灯火点点,天上的月亮又大又圆,忽然觉得这甜不是腻人的甜,是像春夜一样温柔的甜,能把心里的焦躁都化开。
还有一顿晚饭,老陈带我去吃“抬格子”。说是格子,其实是用蒸笼蒸的猪肉和土豆,肉是肥瘦相间的,炖得烂烂的,土豆吸饱了肉汁,又粉又香。吃饭的地儿是个农家小院,桌子是旧木桌,椅子是条凳,旁边还有只老黄狗趴在地上打盹。我夹了一块肉,肥的部分入口即化,瘦的部分也不柴,配着米饭吃,香得能多吃一碗。老陈说,这道菜以前是宜昌人过年才吃的,现在平常也能吃到了。我看着蒸笼里冒出来的热气,闻着肉香和土豆香,忽然觉得,宜昌的吃食就像这里的人,实在、热情,不花里胡哨,却能让人吃得心里暖和。
四、时光在这里,像长江水一样慢慢流
在上海,节奏快得像地铁里的人群,每个人都在赶,赶地铁、赶项目、赶饭局。可到了宜昌,头一天就发现,这里的时光好像走得慢些。
早上在巷子里逛,看见卖菜的大妈不慌不忙地整理着菜筐里的青椒,叶子上还挂着水珠;路边的茶馆里,几个老爷子围着桌子喝茶下棋,棋子落盘的声音“笃笃”响,旁边看棋的人也不着急,眯着眼慢悠悠地抽烟;就连马路上的车,好像都开得比上海慢,遇见行人过马路,远远就停下来等。
老陈带我去三峡人家,那地方在山里,得坐渡船过去。渡口边有个卖茶鸡蛋的老婆婆,坐在小板凳上,面前的煤炉上煮着鸡蛋,水汽“滋滋”地冒。我买了两个,问老婆婆煮了多久,她笑出满脸皱纹:“没看钟,反正水开了就一直煮着,入味。”那鸡蛋煮得确实入味,蛋白是茶褐色的,蛋黄也带着咸香,我蹲在渡口边吃,看着渡船慢悠悠地从江面上开过来,船头撞开的浪纹好久才散开。
在宜昌待了五天,有一天下午,我独自去了趟屈原祠。祠在秭归县,靠着长江,白墙灰瓦, quiet得很。院子里有棵大樟树,叶子绿得发亮,树下摆着几张石桌石凳。我找了张凳子坐下,听着旁边厢房里传来的诵经声,那声音不高,像溪水一样缓缓流淌。“静是福,能静下来的人有福”。在上海,我很少能这样安静地坐着,心里头总有事儿吊着,可在这儿,看着长江水悠悠地流,听着风吹过樟树的声音,竟觉得心里头空落落的,又满当当的——空的是那些杂七杂八的焦虑,满的是这眼前的山、水、树,还有这慢慢流淌的时光。
临走那天,老陈送我去机场,路上我说:“宜昌这地方,真好,不像上海那么挤。”老陈笑了:“各有各的好,你们上海热闹,我们这儿嘛,就是个过日子的地方。”是啊,过日子的地方。宜昌不像上海那样光芒万丈,可它有自己的滋味,像清江的水一样清澈,像山里的雾一样温柔,像萝卜饺子一样实在,像凉虾一样甜润。
飞机起飞时,我隔着舷窗往下看,宜昌渐渐变成一片模糊的绿,长江像条银色的带子,在山间蜿蜒。忽然想起在清江画舫上,看见一只水鸟贴着水面飞,翅膀尖轻轻点了一下水,那水纹一圈圈荡开,好久才消失。宜昌给我的印象,大概就像那水纹吧,不激烈,却在心里头慢慢晕开,让人忍不住想再去看看,再去坐坐,再去尝尝那滚油锅里的萝卜饺子,再去吹吹那带着水汽的江风。
这日子啊,慢一点,也挺好。
发布于:广东省倍顺网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